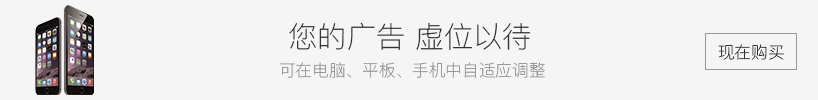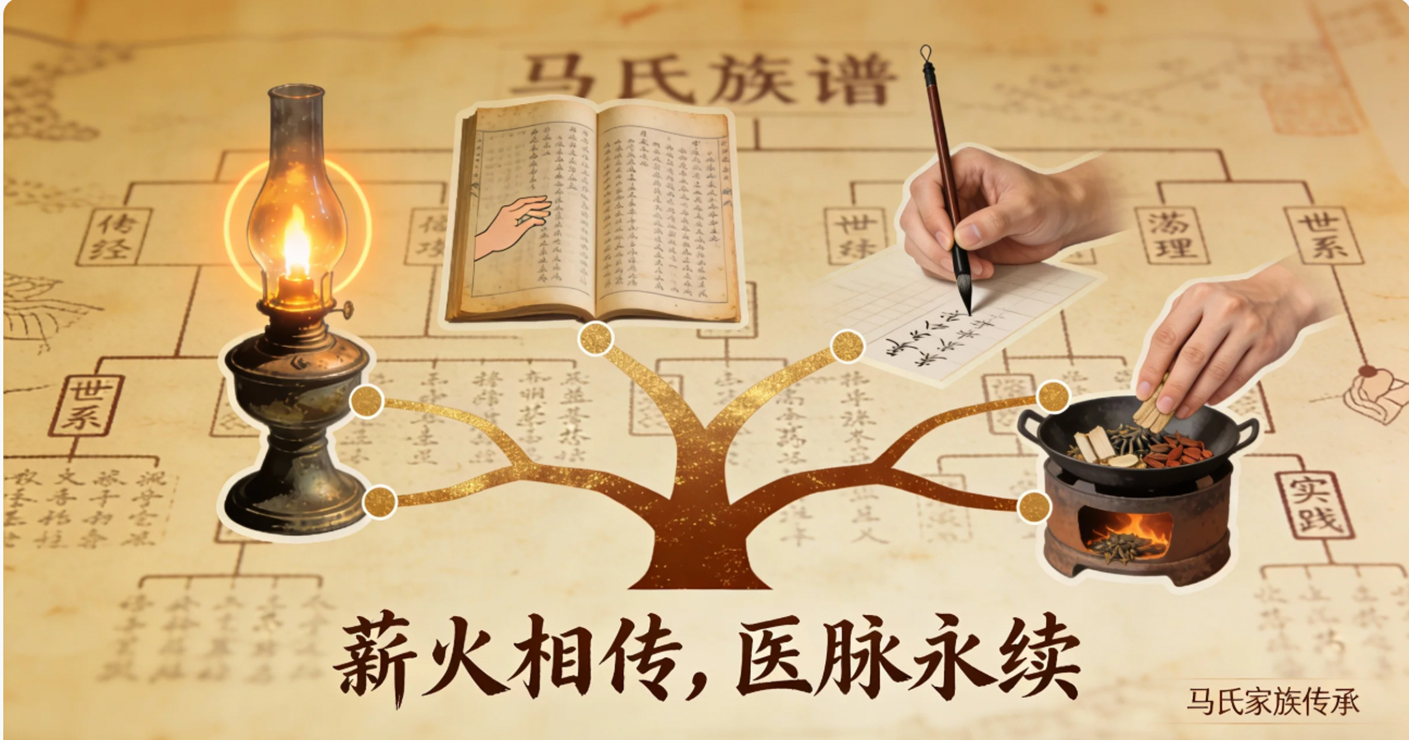1955 年深秋的龙门荒原,北风卷着枯草打在人脸上生疼。范万昌裹紧了旧棉袄,望着身后 150 名犯人、8 名干部,还有身旁背着双枪的妻子翟树荣,声音沉得像脚下的黑土:“先挖地窨子,开春就开荒,咱得在这扎下根。” 这年他 48 岁,鬓角已见霜白,可眼里的光,还像二十年前在抗联队伍里那样炯亮。
没人喊他 “场长”,后来大伙儿都叫他 “老范头”;也没人敢小瞧他身边的翟树荣 —— 当年在北满抗日时,她可是远近闻名,从日本人的北安监狱里 “捞” 出丈夫的 “双枪老太婆”。
一、监狱救夫定终身
范万昌是黑龙江省巴彦县人,1935 年就跟着抗联三军打鬼子。那会儿北满乱得很,土匪 “绺子” 遍地,有的害百姓,有的也跟鬼子拼命。翟树荣的爹就是后一种,手下有百来号弟兄,枪法准得能打穿鬼子的钢盔。
范万昌按党组织的要求,为了联合抗日力量,单枪匹马去见翟老当家。门帘一挑,先瞧见个穿蓝布褂的姑娘,十七八岁年纪,眼亮得像星星,手里把玩着两把驳壳枪 —— 正是翟树荣。往后范万昌来议事,翟树荣总跟着,他在屋里跟老当家谈联合抗日,她就倚在门框上听,他去院子里练枪,她就凑过来比试着瞄准。老当家看在眼里,憋了好几回没开口,范万昌心里也清楚,可抗联的任务压在肩上,哪敢想终身大事?
变故来得快。1937 年,日本人 “并大屯” 清剿抗联,范万昌因为名声太响,被叛徒出卖,被关进了北安监狱 —— 那是鬼子的 “铁牢”。地下党急得团团转,找翟老当家帮忙,翟树荣一听说,当晚就把辫子盘起来,揣了二十发子弹,带着十几个心腹弟兄摸进了北安城。
她早买通了监狱里的杂役,趁着夜黑风高,先用迷烟放倒了岗哨,再用铁棍撬开牢门。范万昌见她浑身是霜,手里双枪还冒着热气,愣了愣,翟树荣却笑了:“范大哥,我‘捞’你出来了!”
这一 “捞”,捞成了一辈子的缘分。当年冬天,翟老当家把队伍交给范万昌,还把女儿许给了他。新婚夜,翟树荣把双枪往桌上一放:“往后你打鬼子,我跟你一起。” 这年范万昌 28 岁,翟树荣 18 岁,夫妻俩带着队伍,南到绥化、海伦,北到龙门,专打鬼子的据点。汉奸都怕他,那会儿汉奸们打赌就说:“我要是瞎讲,出门就遇范万昌!”
二、从抗联英雄到农垦先锋
后来范万昌跟着抗联打了十年,1945 年又参加东北民主联军,当骑兵四团团长,在海伦、望奎一带剿匪;1950 年去了朝鲜,戴着三级勋章回来时,翟树荣抱着他哭了 —— 她知道,“老范头”又从枪林弹雨里活着回来了。
1953 年范万昌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,1955 年接到命令:去龙门建劳改农场。翟树荣没犹豫,收拾了行李就跟着来了。刚进场时,没房子没粮,范万昌带头挖地窨子,翟树荣就帮着烧火做饭,夜里还背着双枪站岗 —— 怕有野兽,也怕犯人跑。
开春播种时,机械不够,范万昌卷起裤腿,跟职工一起拉播种机,绳子勒得肩膀通红也不撒手。翟树荣看在眼里,第二天就把家里的旧棉袄拆了,给大伙儿做了护肩。1956 年 5 月,当拖拉机犁出第一片黑土时,范万昌蹲在地里,抓了把黑土闻了闻,对翟树荣说:“你看,这土能养人啊。”
老范头没文化,就会写五个字,”范万昌批准“,但比圣旨还管用。有个职工想回关里相亲,没钱也没假,就写了张条子找他借钱。老范头只知道人家有难处,大笔一挥写下 “范万昌批准”。后来才知道,那农工写的是 “借五十元”,回来还被他骂了顿。可一听是回去相亲,老范头又笑了:“咋不早说?把媳妇带来农场,来回路费我给你报了!”
三年自然灾害时,农场日子更难。职工们编了段顺口溜:“范场长姓范没饭吃,钱副场长姓钱没钱花,蔡副场长姓蔡没菜炒。” 翟树荣就带着家属去挖野菜、采蘑菇,煮了分给犯人跟职工,自己却总说 “不饿”。有人劝她留着点,她就把双枪往腰里一别:“老范说,大伙儿饿肚子,咱当领导的没脸吃独食。”

三、大义面前不徇私
1963 年出了件大事。农场来了第一台 “东方红 - 54” 拖拉机,编为二号车。范万昌的小儿子才十岁,正是顽皮的年纪,趁驾驶员曹某不注意,爬上了车后的牵引架。没成想履带杆勾住了腰带,等曹某发现停车时,孩子已经被压在了履带下。
大儿子一听弟弟没了,拎着匣子枪就往外冲,喊着要打死曹某 —— 那会儿农场管教干部家都有武器。范万昌追上他,“哗啦” 一声拔出枪,枪口对着大儿子的胸口:“你敢动他一下,我先毙了你!”
翟树荣赶过来时,眼圈通红,却没哭出声。她拉住要拼命的大儿子说:“孩子不懂事,爬上拖拉机是他的错,曹师傅没责任。” 后来场里要处理曹某,范万昌把手一挥:“不怪他,是我没看好孩子。” 这事传开后,职工跟犯人都服了 —— 老范头连自己的娃没了,都不徇私,这样的领导,信得过。
四、双枪传奇留美名
范万昌夫妻俩的枪法,在龙门农场是出了名的。1955 年押解犯人来农场时,路上山高林密,怕有人逃跑。正走着,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,范万昌跟翟树荣对视一眼,同时拔出双枪。“砰砰” 几声枪响,三只大雁直直落下来,犯人都看傻了,一路没一个敢动歪心思。
还有回跟场里的钱副场长、蔡场长比试枪法。几人沿着旧铁路走,钱副场长提议打电线杆上的瓷瓶。钱副场长抬手一枪,瓷瓶 “哗啦” 碎了;蔡副场长也不含糊,第二枪也中了。轮到老范头,他瞄了一下,“砰” 的一声,电线断了。他摸着后脑勺笑:“我这枪法,比你们俩好 —— 专打电线!”。大伙儿最想看的是翟树荣的枪法。有人起哄:“林大姐,露一手呗!” 翟树荣一开始推辞,说 “好久没摸枪了”,最后还是架不住劝,才说:“拿我枪来。” 两把德国造的驳壳枪递过来,她微微蹲下,弹夹往大腿上一磕,“咔咔” 两声,子弹就上了膛 —— 没人看清她是怎么动作的。
她让人从高粱秸堆里抽了一根,喊了个年轻职工:“你拿着,站到50米外。” 那职工刚站定,就听 “乒乒乓乓” 一阵枪响。等枪声停了,职工手里的高粱秸已经短了半截,打下来的每截都一样长,像用尺子量过似的。大伙儿围上去看,都咋舌:“翟大姐这枪法,还是当年的‘双枪老太婆’!”
1964 年春天,范万昌接到调令,要去安达畜牧局工作。走的那天,农场的职工、家属都来送,有的手里攥着刚蒸的窝头,有的抱着自家种的土豆。翟树荣背着双枪,跟在范万昌身后,回头望了望那片已经种满庄稼的黑土地,八年里,他们在这里开荒五万多亩,建了学校、医院、砖厂,曾经的荒原,已经成了有烟火气的家。
后来有个老职工说,老范头走后,翟树荣又回来过一次,她没惊动任何人,只和他们几个老同志见了个面,在当年挖地窨子的地方站了半天,又去儿子出事的拖拉机旁看了看,最后对着农场的方向,敬了个军礼。(张加忠 赵长勇)